第一百三十八章 庆生
第一百三十八章 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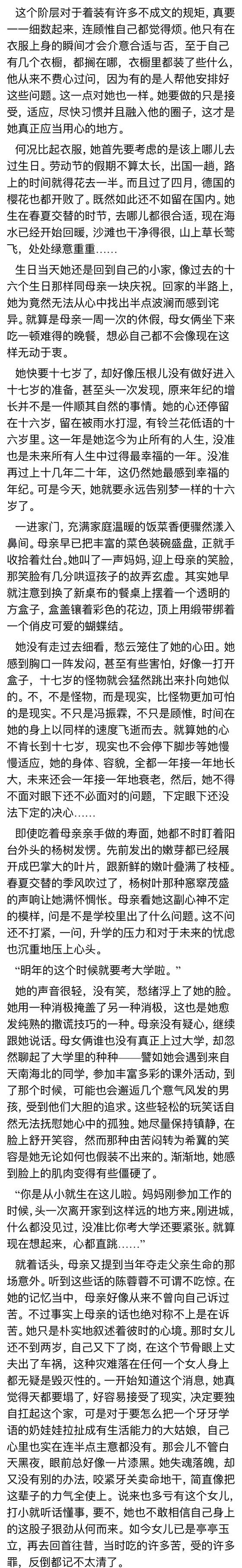
今天是她又长大一岁的生日,母亲的这番告白自然饱含欣慰。然而不同寻常的是,在那朴实的语气下,她竟还隐隐听出一股平日里没有的畏葸。不,也许不一定是没有,而是因为过去的她还无法对这种畏葸感同身受。这是没有经受过痛苦的人绝对听不出来的畏葸。这一发现加重了她的吃惊。她意识到一直一来,自己对母亲的体谅都仅停留于浮浅的表面,只要一说起母亲辛苦,她的第一反应就只能想到身体的辛劳罢了。但,即便身上的辛劳会随着时间淡忘,可是痛苦留下的疮疤,历经多年都还会清清楚楚地刻印在心中。这是她从一年的痛苦当中,从不仅有雨水和鲜花的十六岁中学会的道理。在不久的将来,她还会经受更多这样的痛苦,并且从这更多的痛苦中,会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爱。
她揭开了生日蛋糕的盒盖,蛋糕的表面铺满了温柔的白色nai油,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在森林中嬉戏,她的眼睫下不觉蓄满了泪水。
她已经十七岁了。
这天,顾惟照样过着从休假开始以来的闲适生活。陈蓉蓉一早上学的时候,他倒是陪她去了一趟学校,当然不是去上课的,只是去处理几件杂事。尽管他跟父亲还没有定好究竟是回欧洲还是去美国,不过明年出国的计划肯定不会变。说实话,他想暑假的时候就直接出去,省得入学和毕业都挤到一块。一旦确定了大学,后头的事会就一件接着一件。像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倒可以交给陆伯跟鹤姨解决,但是家族资产的分散,产业的扩展,还有新的交际圈没有一样能假他人之手。
学校中午十二点就打了放学铃,以便学生能提前过上劳动节的假期。事实上有不少人从两三天前就开始请假,只有她还老老实实地待到最后一刻。今天出城的车流想必很拥挤,不知她几点才能到家。他信手弹着舒曼的《童年情景》,脑海中忽然闪现出陈蓉蓉透过车窗向外眺望的脸,这是他在钢琴声中浮想联翩的众多片断里,唯一留下记忆的一个。
午觉起来他去了健身房,练了一个半小时后,出来洗了个澡。女仆照他的要求把下午茶摆到休闲室里,他随便吃了几样东西,在那儿登录了很久没碰过的游戏。
玩不到十分钟,游戏的音效陡然弱了下来,电话接听的提示出现在投影屏幕上方,冯振霖这三个字毫不客气地遮住了角色在跑动过程中不断切换的游戏场景。顾惟手柄不停,挂着耳麦接起了电话。
喂。
在干吗?
打游戏。
你一个人打?
嗯。
Cao,干吗不叫上我?
你有时间吗?
废什么话!
电话那头传出一阵叮咣杂乱的声响,不多时,他收到了冯振霖发来的联机邀请。两人挂掉电话,一边Cao作着角色,一边在游戏上开麦闲聊。
我以为你爽得找不着北了。
冯二少呿了一声,对他的话嗤之以鼻:
你这人也真是怪,有时间打游戏,没时间过来玩。
怎么,不就是性冷淡吗,跟兄弟还哎CaoCaoCao,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快来掩护爸爸!
冯振霖说的玩,指的并非是像以往那样上乐巢去找乐子。前段时间,约莫是瞧他性情大变吧,家里人终究还是松了口,给他在自己的别墅里办了一场泳装派对。用的是庆生的名义,不过现场谁都不准提像成年啦,家业啦,订婚啦之类的字眼,这是冯二少定下的奇怪的规矩。更奇怪的是他们三个发小一个都没到场,他居然不像以前那样闹腾个没完,这也跟他总是喜欢扎堆凑人气的一贯秉性大不相符。